弘扬教育家精神笔谈 | 从稷下学宫看教育家精神
稷下学宫,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,始建于齐桓公时期(约公元前374年),历经150余年,汇聚了天下最顶尖的学者,孕育了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“百家争鸣”,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和人才培养的摇篮。稷下先生并非是空谈玄理的隐士,而是怀抱“以其学易天下”的入世情怀,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治理、社会发展紧密结合,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教育传统,其独特的教育精神,在当代教育实践中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。
一、“道术为公”与心有大我、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
稷下学宫的“道术为公”,本质上是一种“超越个体、指向公共”的价值取向,与“心有大我、至诚报国”的理想信念有着深刻的精神同源性与逻辑延续性。一是超越学派之争的共同体意识。稷下学宫汇聚儒、道、法、墨等各家学者,虽观点不同,但都以“弘道济世”为目标。这种超越门户之见、共谋天下治理的格局,体现了“大我”的胸怀。如孟子倡导“仁政”,虽与法家思想对立,但根本目标仍是解决战乱时代的民生困苦。二是“士志于道”的责任感。稷下学者并非仅为发展个人学术成就,而是通过著书立说、参政议政影响诸侯政策。这种以学术服务社会的使命感,与“大我”精神一脉相承。三是乱世中的救世情怀。战国纷争背景下,稷下学者普遍怀有“平治天下”的理想。如邹衍的“五德终始说”,试图以历史规律论证统一趋势,间接为结束战乱提供理论依据。
二、“不治而议论”与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
稷下学宫“不治而议论”的学术传统与“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”的道德追求,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精神的重要源头,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学术生态与士大夫伦理。一是道统与责任的结合。稷下学者虽学派林立,但核心道德观深受儒家影响。孟子曾游学稷下,其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主张,为“士则世范”提供了伦理基础。二是学术与政治互动。稷下先生“以道议政”,既保持相对独立的学术立场,又通过“议政”成为国家“顾问”,形成“官办学术、民间议政”的特殊形态。如淳于髡“微言讽谏”齐威王的故事,展现了以智慧劝诫君主的经典案例。三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基因。这一学术传统形成了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参与准则,有效平衡了“政统”与“道统”的互动模式,为古代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纠错机制与理性空间。
三、“学术自由”与启智润心、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
稷下学宫的“学术自由”与“启智润心”的育人目标、“因材施教”的教学智慧深度融合,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独特的“育全人”传统。一是思辨启智的教育智慧。学术自由的“无学派壁垒”打破思维定式、训练“主动思考”能力;“无言论禁区”使人解脱教条束缚,培养“批判自由”精神;“无身份限制”打破出身贵贱、国籍差异的“平等自由”,为“因材施教”提供了天然场景。二是“自由辩论”倒逼学生主动构建认知体系。师生常以诸如“性善”“性恶”为核心议题展开交锋,这种“不盲从、敢质疑”以“打通知识壁垒”的过程,正是“以名举实,以辞抒意,以说出故”之意,更是稷下“启智”(《墨子·小取》)的方法论。三是自由学术下“顺其性而育之”。稷下学宫的“因材施教”实则依托学术自由形成的“自然分流”与“个性化引导”,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与资质“选课”,本质是“让学生自主匹配最适合的成长路径”。同时,稷下先生会依据学生的性格、认知特点“因势利导”,如孟子的“类比启发”、荀子的“礼法并重”、慎到的“逻辑推演”等方法,通过自由氛围让“适合的教育”自然发生。
四、“经世致用”与勤学笃行、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
“经世致用”的本质是在扎实的学识与切实的实践基础上,围绕“学术为现实服务”展开。一是现实问题的复杂性,须以深厚的学识为前提。稷下学者或钻研古籍、或探究自然与社会规律、博采众家之长,这种“勤学不辍”的精神正是为了“兼济天下”储备知识工具。二是锚定学术的现实导向。稷下学宫具有教育、科研与为政治服务的功能,学者们围绕各种主题展开讨论,为国家提供政治咨询和建议。这种“学术与政治互动”使教育超越了纯粹的知识传授,体现了“学问生于需求,教育归于实用”的精神。三是学术思想创新和追求真理精神。稷下学宫倡导学术自由,各学派之间相互争辩、诘难,不但展示各自的理论优势,也不断修正、完善自身学说。如荀子吸收了法家、道家等思想,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创新和发展。
五、“传道济民”与乐教爱生、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
“传道济民”既传“治国之术”与“为人之道”,更强调以学术关怀民生,服务社会。一是平等的师生关系。“先生”与“学士”是“亦师亦友”的关系,如荀子不仅对弟子的困惑耐心解答,甚至在弟子遭遇困境时给予支持。稷下学宫兼容百家,学生可自由择师,学者们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,而是鼓励“各言其志”,以尊重个体的成长规律。二是以讲学为乐,视教育为使命。稷下学者将教育视为“传道”的核心途径,以讲学为乐,将教育视为终身事业。如荀子“三为祭酒”,年近七旬仍坚持讲学,弟子遍布天下;孟子即便仕途不顺,仍以教育延续“传道”使命,体现“乐教”的自觉。三是不计名利,以理想为先。稷下学者不将名利视为追求,而是以“传道济民”为终极目标,甚至为坚持理想拒绝高官厚禄。如孟子曾拒绝齐王的“万钟之禄”,始终坚持对“仁政”理想的追求。
六、“兼容并蓄”与胸怀天下、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
稷下学宫将“救天下”的现实使命与“塑人心”的人文理想结合,为中国文化注入了“胸怀天下、担当道义”的基因。一是实现长治久安的“天下之道”探索。稷下学者秉持学术议题的“天下性”、学术立场的“超越性”,如孟子的“仁政”、荀子的“王霸之辩”、黄老学派的“道生法”等,探索“何为理想的天下秩序”。二是教化塑造理想人格。稷下学宫以培养“明道理、知善恶”的人才为核心,将“天下关怀”内化为士人的精神品格,再由士人影响社会与政治,以实现“天下之道”。三是以思想之力塑造天下。尽管学派林立,稷下学者始终在寻找思想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如普遍认同“止战、安民、富国”为“治国之道”,及“如何通过教育引导人性向好”的“人性”指向等。这种“求同存异”超越了学派之争,在多元中寻找“天下秩序”的“文明共识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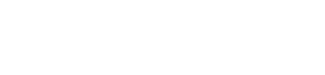
 联系电话:0533-2787701
联系电话:0533-2787701
 地址: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266号鸿远楼1007
地址: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266号鸿远楼1007
 邮编: 255000
邮编: 255000
 邮箱:jsgzb@sdut.edu.cn
邮箱:jsgzb@sdut.edu.cn